发布日期:2025-04-29 21:46 点击次数:137

文|武晓雨 股票实盘配资平台排名
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曾对“地方”的概念做过这样的论述:“大到一座城市,小到小区门口的街道,都是地方的不同类型——地方构筑起人们居住的周围世界。如果说空间意味着一种陌生感和新奇感,地方就意味着一种熟悉感和亲密感,因为后者是以我们自身的实践活动为圆心建造起来的,它容许我们筑造和栖居。”
作为一部旅行文学,《小地方》探讨人与地之间的隐秘联结,特别是“筑造和栖居”过程中,人地关系的变化和流动。作者李昊从漫游者与造城者的身份、经历和情感体验出发,结合城乡规划、人文地理的相关知识,记录下小地方的凡人微事,将关于城乡发展和变迁的主流宏大叙事,转化为人和个体的尺度的感知。这不是一部传统的旅行文学,而更应称为“新旅行”式的书写,将游记、散文、评论糅为一体,形成了崭新的文类。所谓新旅行,即一场下沉到日常生活中的“City Walk”,由此也产生了跳脱出职业身份的微观察和深洞见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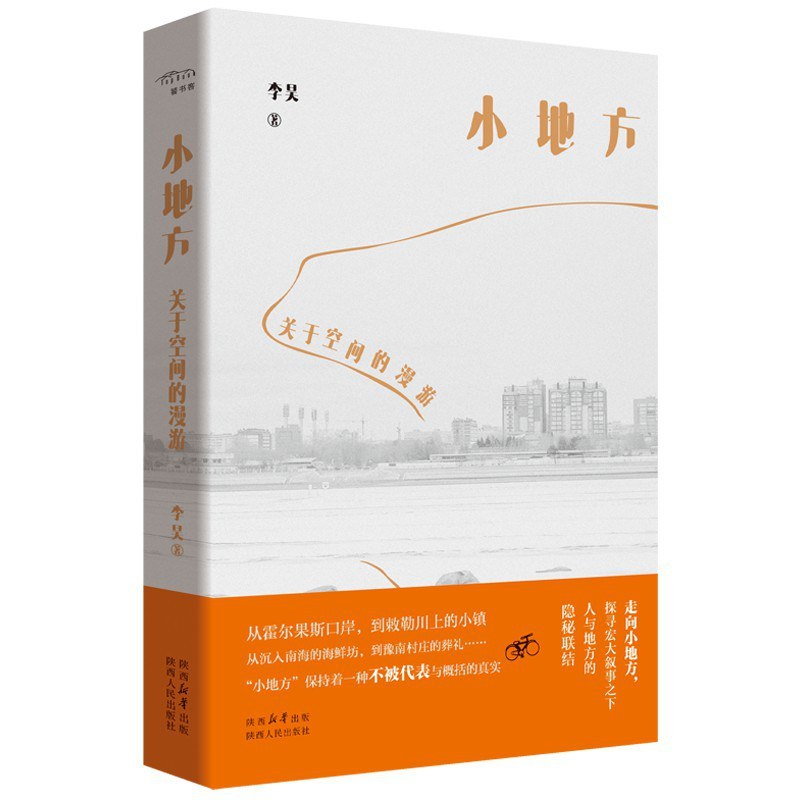
在李昊看来,“小地方”的含义具有双重性。一是指向地域概念上的“十八线”小城、基层、乡镇、村庄、原野,这些地方名不见经传,处于现代化进程的边缘。二是颗粒度上的,指向都市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细节、平凡的事物、难言的情愫,这些寻常角落里的细微生活,都隐匿于宏大叙事的背后和主流镜头之外,难获镁光灯所照见,但它们却生动又具体,保持着一种不被代表和概括的真实。
铁桥取代木桥,商铺取代淫祠,大型轮渡取代古朴而和缓的木造渡船,显示出现代化进程的无可抗拒。正如《德萨科塔》中的浙南村庄,农地与厂房、村舍与楼宇,拼合出灰色边缘地带里一幅形象模糊的城乡景观,挖掘机与搅拌车带来了古典审美与田园人居的瓦解,以及工业文明对传统农业文明的进犯。但村庄的生命力不会消失,人的历史不过是大地历史的一瞬,无序的构建兴许会在未来诞生出一个新的令人迷恋的江南。
告别德萨科塔,再回到都市文明地带,李昊在水泥钢筋的缝隙中,同样窥见了被集体视野所忽视的文化空间。《成都范特西》是二十一世纪的“东京绮梦”,资本与流量重塑着城市的发展,互联网经济与城市企业主义的结合催生出新的文化认同,并带来城市意象的改变。城市的“余味”,或被称为“烟火气”的东西日渐稀薄,它提示着一种质朴的生活因子正在慢慢消失,而传统的变迁就发生在夜店与茶馆之间。与此同时,流行文化的同质与量产不断为城市添附新的标签,千城一面的公共生活场景也在无形中加剧着地域感的丧失。
作为一名城市规划师,李昊有着自己对于这一浪潮的审思。他在老城区中停停走走,对空间细节的变化始终作温和的凝视,并试图在后现代性越发汹涌的当下探寻社会学家古德纳所提出的“日常生活的对抗意义”。于是,他在酒吧街上的中老年人、姑娘身上三星堆的文身、本地方言中,看到和听到了一座城市对自我的坚持。这些无法被机械化造城运动磨去的精神追求、审美况味和地域习惯,构成了城市原初的社会性和文化基因。不是流量或标签或其他什么,正是“日常生活建构了它自己的真实”,一种难以通过图表和报告可视化的本地人的生活真实。
同样深受都市性的召唤,较之成都,《回龙观》这个北京城中的“小地方”,则贮存着更多异乡人对于世界的细碎感知。这里在现代化进程中一度被悬置、与城市繁华擦肩而过,却是无数“北漂青年”的床榻,是他们“短暂的一个故乡的家”。李昊将目光投向异乡人的生存现实,以人本的尺度和人文的温度重新审视边缘地带的内涵,以及人与地发生关联的方式。回龙观里久未进城的青年与强势的房东,个体的紧张、憧憬与挣扎,构成了时代褶皱里严酷与希望并存的情感记忆。
在李昊看来,建筑、景观与街道都有可读性,风景就藏在日常的生活里。而当宏大成为主流叙事的核心,当千城一面成为城市化大潮的必然趋势,当互联媒体和工业技术钝化了人类切近的感知力,当世界大同把遥远的所在筑成当下的生活,“时间在变,空间在变,留下的只有记忆打磨后的人地关系”。于是他呼吁:下沉下去,到小地方去。为从细枝末节中触摸事物丰富的肌理,为在边缘情境中寻找未被定义的生活真相,为建立不受公共话语侵蚀的私人表达,更重要的是为发现人,下沉下去,到小地方去。
客观世界问题的最终指向都是人。“外面的进行着的夜,无穷的远方,无数的人们,都和我有关。”
“我存在着,我在生活,我将生活下去。”
作者为书评人